翻譯:36Kr/boxi
36kr.com/p/5194729
原文:https://www.linuxjournal.com/content/25-years-later-interview-linus-torvalds
編者按:1994年,《Linux Journal》創刊。當時雜誌的特寫文章是雜誌的第一位發行人Robert Young(後來與人聯合創辦了Red Hat)對Linus Torvalds(Linux內核的作者)的採訪。25年之後,兩人再度坐到了一起,就Linus本人的近況,Linux的成功之道以及未來之路,自己的工作哲學,對社交媒體的看法,對網路噴子和匿名性的態度,對年輕開發者的建議等進行了推心置腹的交流。本文作者是Robert Young,原文標題為:25 Years Later: Interview with Linus Torvalds

Robert Young 與Linus Torvalds的訪談錄
Robert Young:很高興能有個藉口跟你取得聯絡。你跟家人都挺好的吧?你的孩子現在應該都上大學了。我和Nancy還有我們的3個女兒都挺好。我和Marc創辦Red Hat的時候老大Zoe 11歲,現在她準備有第二個孩子了——也就是說,我現在都當爺爺了。
Linus Torvalds:其實我的孩子都還沒大學畢業,不過Patricia(老大)今年5月會畢業。Celeste(最小的)在讀高三,所以再過半年我們就成空巢老人了。
3個孩子都還不錯,當外公我想/希望是幾年後的事情了。
Bob:1994年我第一次採訪你時,你會不會認為到 2019 年自己還會維護這個東西?
Linus:我想1994年的時候自己就已經感到驚訝了,想不到我的最新專案不僅僅又是一個“做點有趣的直到它做了我需要的一切然後再找點別的去做”這樣的專案。當然,那時候還處在開發相當早期的階段,但那已經是我做了幾年的專案了,並且已經有了自己的生命。
所以我想我試圖要表達的是,我未必會預料到會再做它幾十年,但它已經邁過了一道坎,成為我生命當中一個相當重要的東西。其實我從來都沒有給Linux制訂過長期計劃,我做事都是一天天來的,而不是考慮5年或者10年後的事情。
Bob:關於實現你的夢想的危險性,你過去有一句名言——在被問到對Linux的未來標的是什麼時,你經常開玩笑說是“統治世界”。現在你還有更廣大的開源/免費軟體圈已經實現了這個標的,接下來呢?
Linus:呃,我很久以前就不開“統治世界”的玩笑了,因為隨著時間推移這個看起來不怎麼像是玩笑了。但它一直都是個玩笑,這也不是我(或者任何其他開發者)做所做的事情的原因。那個原因永遠都只是為了做出更好的技術,去發掘有趣的挑戰。
其實在核心層面沒有一樣東西改變。所有的細節都變了——硬體已經很不一樣,我們的問題已經很不一樣,我的角色已經很不一樣。但“做得更好,發現有趣的挑戰”依舊不變。
比如說,1994年那時,我基本上是個開發者。當然,我也是首席維護者,但雖說我花了很多時間在合併補丁上,但我基本上都是寫自己的程式碼。現在我很少寫很多程式碼了,而且我寫的往往是偽程式碼或者樣例補丁,然後發郵件給真正的開發者。我曾經對把自己叫做“經理”猶豫過,因為其實我並沒有做過年度考評或者預算之類的事(感謝上帝!),但我絕對更像是技術領導而不是實際的程式員,過去許多年裡一直都是這樣。
所以真正重要的東西沒有變過,但跟1994年相比,我的角色以及所有那些細節,顯然已經非常非常不一樣了。
Bob:再過25年,你以及這個程式碼庫會去到哪裡?
Linus:呃,那時候我都75歲了,我懷疑到時候還能不能每天都這麼投入。但考慮到我一直做這個都快30年了,也許我屆時還會跟進下去。
好訊息是我們的確有一個非常堅實的開發者群體,我不擔心“Linus會走向何方”之類的問題。當然,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大家一直都在討論核心開發者怎麼變得越來越老的問題,但這其實不是因為我們找不到任何新人,而完全是因為我們依然有很多做了很久的人還在做,並且仍然享受其中。
我曾以為有朝一日會有個令人興奮的全新OS出現,取代Linux(嘿,1994年那時候我大概仍然認為也許Hurd會做到這一點!),但我們不僅做這個做了很長一段時間,而且仍然做得非常好,我也意識到開發新的作業系統要比我想象的難多了。這的確需要很多人付出很多努力,而Linux——或者更廣大的開源——的優勢,正在於你可以站在別人的肩膀上做開發。
所以,除非技術版圖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否則的話我認為Linux再過25年依然會做得相當好。這不是因為程式碼本身的任何細節怎樣,而完全是因為其開發樣式和問題空間使然。
到那時候我可能幹不動了,而且很多程式碼都會被升級替換,但我認為這個專案仍將保留下來。
Bob:這些年來為了讓你滿意,你和核心團隊是不是一直在更新核心程式碼?已有25年曆史的不斷擴張的Linux程式碼庫是否存在重寫的需要或者壓力?是不是可以用比C語言“現代”一點的語言來重寫?
Linus:這些年來我們已經對大多數子系統進行了很多的大規模重寫——當然不是一次性地——很多程式碼塊最終都已經成為了沒人再想去修改的了(通常是因為那是過時硬體的驅動程式,已經很少人用,但我們還將支援)。不過,整個內核有一個大一統的程式碼庫的好處之一,是當我們需要做出一些大的改變時,我們就能做到。可能有一些核心之外的驅動程式等(包括原始碼和二進位制檔案),但我們一直以來的政策都是,如果是內核以外的話,就不關開發的事。所以,必要的時候我們可以做出徹底改變。
至於C,沒有比這更好的語言出現。我們已經針對新的改進過的功能更新了核心原始碼(在這些年裡C 語言本身也發生了變化),而且我們還為額外的型別檢查、執行時驗證以及強化等給C 語言上添加了各種擴充套件,但基本上除了一些小細節之外,這門語言基本上還是一樣的。
而且說實話,這看起來不大可能會變。大家看到處在活躍開發中的那種語言不是用來進行底層系統開發的,而是為了讓用好看的UI等開發使用者應用更容易而準備的。這類語言顯然不想乾核心需要的事情,比如底層人工記憶體管理等。
可以想象,我們會有一些“框架”語言來生成驅動程式或類似東西,而且在我們內部實際上也有自己的簡化“語言”來進行配置,我們在建構過程中的確也使用了一些其他語言,所以C不是我們使用的唯一語言。但到目前為止,這是大部分都是用C寫的,“真核”都是用C來寫的。
Bob:你選什麼樣的硬體?是不是那種Linux(或任意其他)筆記本牌子貨?還是平板或者手機?
Linus:我的主要開發裝置是非常普通的PC工作站。那是這些年來組裝起來的。機器沒什麼特別,自打我對它大改之後其實已經有2年了,所以甚至都算不上先進。在家裡我的主要要求其實就是要徹底的安靜。除了幾個風扇以外,裡面沒有任何的活動件(所以再也沒有機械硬碟了),而且風扇大部分時間內甚至都不用轉。
外出時(幸好不用經常),我的主要需求是螢幕要好、要夠輕。我的標的重量是1公斤(帶電源),說實話,我還沒有達到這個理想標的,但目前對我來說最好的折衷是 XPS13。
Bob:似乎Linux在桌面的成功不在於PC桌面而在於(透過Android實現的)裝置桌面。你怎麼看?
呃,傳統PC顯然不再像以往那樣佔主導了。哪怕你一臺電腦(即便仍跑 Windows或OS X),很多人也主要是透過web瀏覽器和一些應用程式來使用。當然,還有那種“工作站”使用者,這是那種我個人一直設想中的桌面。雖說還很重要,但它似乎已經不能像當年的PC那樣去推動市場發展了。強大的臺式機似乎主要是用來開發、玩遊戲、或做媒體編輯。那種“休閑”類桌面似乎更多是瀏覽器類的東西,而且往往只是一臺平板或者手機。
當然,Chrome在其中某些領域似乎做得不錯。不過就每天都跟Linux打交道的人數而言, Android顯然佔了大塊頭。
[Bob註:就“統治”的嚴格意義來說,這可能是公平的。但儘管過去幾年PC總出貨量有所下降,但1994年到2014年PC市場的累積增長依然可觀,以致於即便在PC市場放緩的今天,每年PC的安裝量仍然是1994年的4、5倍]
Bob:如果你得解決網路世界的其中一個問題,那會是什麼?

Linux之父(Linus Torvalds)
Linus:都不是技術性的問題。但是,我對現代的“社交媒體”深惡痛絕——如Twitter、Facebook、Instagram 等。這是一種病,似乎鼓勵了壞行為。
我認為其實郵件也有部分同樣的問題,我之前曾經說過:“在網際網路上,沒人能聽得出你的微妙”。只要不是面對面的交流,你就會錯過所有正常的社會線索,很容易就會錯過幽默和挖苦,但也很容易就會錯過對方的反應,所以就會有吵得不可開交等面對面交流不易出現的情況。
但電子郵件仍然管用。你仍然必須花精力去寫,而且一般都會有一些實際內容(技術性或者其他)。那些“點贊”和“分享”之類根本就是垃圾。不用付出,也沒有質量控制。實際上,這些都跟質量控制都是背道而馳的,大家標的的共同點最少,都是些標題黨,是為了喚起情緒反應,往往是道德義憤之一。
再加上匿名,這完全是令人作嘔。當你甚至都不把真名寫在你的垃圾(或者你分享或點贊的垃圾)上時,的確是一點作用都沒有的。
其實我是認為匿名性被高估的人之一。一些人將隱私與匿名混為一談,認為這兩者是息息相關的,保護隱私意味著你需要保護匿名。我想這是錯誤的。如果你是告密者的話匿名是重要的,但如果你無法證明自己的身份,你在一些社交媒體平臺上的瘋狂謾罵就不應該可見,而且你也不應該能夠分享它或者點贊。
好吧,我這也是謾罵。我不上任何的社交媒體(我試過一段時間的G+,因為上面的人不是腦殘,但顯然它從來都沒火過),但這依然令我困擾。
Bob:本期的《Linux Journal 》關註的是孩子與Linux。對於年輕的程式員/電腦科學學生你有什麼建議?
Linus:其實我是最不應該問的人。我知道自己很小的時候就對數學和計算機感興趣,直到大學之前我基本上都是自學的。我做的一切差不多都是自發的。所以當大家說“我應該做什麼?”時,我不能理解大家面臨的問題。我根本就沒有這樣的問題。
Bob:你我的第一次見面是在DEC展上。在“瘋狗”Jon Hall和DEC的資助下,那是你第一次去美國。
我認為那其實是我第二次到美國。我想第一次是去猶他普洛佛,跟Novell 討論 Linux(為了Novell的一個內部專案,是Caldera的前身)。
不過DECUS展(是在新奧爾良嗎?也許我記錯了)的確是我最早到美國的目的地之一。
Bob:我曾經問過你回到赫爾辛基時是怎麼處理掉積壓的電子郵件的。你的回答令我感到吃驚,後來我一直都取用你說的話。你只是說你會把積壓的郵件發往/dev/null。我表示震撼並且問你:“如果收件箱有重要郵件怎麼辦?”你聳聳肩回答道:“如果是重要的話,寫信的人會再發一遍的。”這可能是任何人能給我的最釋懷的建議了。你現在還遵循這種郵件處理哲學嗎?
Linus:多少還是這樣的,但與此同時,我的工作流已經改變了很多,所以旅行不會像過去那樣對我的工作造成那麼大的幹擾了。所以一這段時間以來我往往會儘量不讓大家註意到我出去了。如果在1、2天內我的網際網路連線可能有問題的話(尤其是如果你是水肺潛水員的話)我會提前警告一下。但大多數時候,我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幹活。我試過把行程安排在合併視窗期以外(有時候會失敗),因為那這是我收到pull請求最多的時候。
所以這段時間我都是把郵件存在雲端,這樣子機器間切換就容易多了,這也意味著當我旅行並且使用我的筆記本時,不再會像過去那樣下載郵件到本地機器那麼痛苦了。
而且不僅我的郵件是這樣——實際上,幾乎所有的核心開發最終都是靠git來分發的,這也意味著我在哪臺機器上基本上已經不是問題,而且同步要比過去透過電子郵件一個個去處理補丁容易多了。
不過,我那個“如果郵件重要,對方會重新傳送”的看法依然有效。大家都知道,我差不多是全年輪軸轉的,如果我幾天內都沒有對pull 請求做出響應的話,這仍然意味著它可能會被埋沒在我一堆郵件當中,大家就會再發一封郵件來提醒我一下。
但這種情況其實已經比過去少見多了。1994年的時候,我還沒那麼工作過度,離開一週也沒什麼大不了的,但是,在接下來的幾年裡,情況慢慢變得越來越糟,以至於我們以前那種郵件發補丁的工作流意味著我有時被迫忽略補丁,因為我已經沒有時間去處理,且知道大家還會再次發郵件的。
很高興,那樣的時光早已一去不復返。BitKeeper對我產生了很大的的影響,儘管不是所有的維護者都喜歡它。現在git意味著我不再透過郵件收取成千上萬的補丁,我的收件箱看起來不再像過去那麼糟糕了。所以跟它相處也容易些了。
順便說一句,有一條規則可能比“如果郵件重要,對方會再次傳送”還要重要,我已經執行力很長一段時間:如果不必回覆,那就不回覆。如果我收到郵件後的反應是別人可以處理的話,我會幹脆忽略這封郵件。一些日理萬機的郵件人會設定自動回覆說“抱歉,我最終會處理的你郵件的”。但我會忽略任何自己覺得與我無關的事情。這麼做純粹是因為我覺得我承受不起鼓勵大家給我傳送梗更多郵件的後果。
所以我收到很多郵件,但其實大部分我都不回的。實際上,我的工作很多都是掌控全域性,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所以我會看很多郵件,但一般不怎麼寫郵件。
Bob:1995年5月,Don Becker在華盛頓組織的一場Linux使用者組會議中,你發表過一次演講,中途你曾停下來問聽眾誰知道男子冰球世錦賽芬蘭對瑞典的比分。作為與會的加拿大代表,我得以向你保證芬蘭贏得了比賽。說道這個,芬蘭最近贏得了世界青年錦標賽,你肯定感到很開心。還是你會為美國歡呼?
Linus:嗨!冰球也許是芬蘭的國球,但我不是狂熱的體育迷。搬到美國並不意味著我會選棒球或者橄欖球,只是意味著冰球也失去了那種“我周圍的人在乎”的感覺。
Bob:我們很多人都對你在Linux技術決策的公開辯論中直言不諱的態度感到欽佩。嗯,其他人就不喜歡你直率的說話風格。隨著時間的推移,你認為自己是不是多多少少有了一些外交辭令的味道了?
Linus:如果說有什麼區別的話,我想我已經變得更安靜了。我不會說這是“更加外交辭令”,但也許是更有自知之明瞭,而且我也在試著不那麼咄咄逼人。
這部分是因為大家不再像過去那樣對我進行解讀。過去的環境更加隨心所欲一點,我們也是一群享受樂趣的極客。現在的環境跟過去不一樣了。再者也不像過去那樣個人化了,現在參與開發的人已經成千上萬,這還只是計算量發出補丁的人數,還不是做Linux的人的全部。
而“用不同的方式解讀我”的部分原因在於,大家用一種1994年時不曾有的嚴肅態度來對待我。這絕對不是抱怨說當時大家沒有認真對待我——其實恰恰相反。這更多是我的抱怨,抱怨大家現在太過認真地對待我了,所以我再也不能說一些愚蠢的廢話了。
所以我仍然會號召大家(尤其是公司)做些蠢事,但現在我這麼做的時候必須知道這是新聞,如果我朝某些公司豎中指的話是會被記住幾十年的。不管是否活該,這種行為可能都不值得。
Bob:你還有什麼要說的嗎,無論是公開或者私下?
Linus:我從來都沒有想要傳播的“訊息”,所以……
關於Robert Young以及過去25年他的經歷
1976年,Young學習歷史後從多倫多大學畢業,然後找了一份賣打字機的工作。1978年,他創辦了自己的第一家公司,然後再加拿大獃了15年,掌管著兩家計算機租賃公司。他把第二家賣給了一家更大的公司,1992年後者派他渠道美國的康涅狄格州來發展美國的子公司。很快,新的母公司遇到了財政困難,也就是所謂的破產,Young開始自主創業。

Robert Young,Linux Journal的第一位發行人
儘管這一事件直接導致了1993年 Red Hat的誕生(跟北卡羅來納州的軟體工程師Marc Ewing一起創辦),但兩人均愛上了自由軟體——也就是現在所謂的開源——Ewing愛上開源的原因是他可以用帶原始碼且授權允許他創新的軟體來創新,Young的原因則是他看到跟比專屬軟體相比,開源技術可以更好地服務技術客戶。自從創立到1999年上市一直擔任RedHat CEO的Young後來專任主席,出色的Matthew Szulik接任了CEO,將早期的Red Hat打理成一門出色的生意。Red Hat現在已經是代表美國最大上市公司的標普500指數的成員。
2000年,Young和Ewing聯合創立了Center for Public Domain,這是一個促進智慧財產權、專利及著作權法健康交流,以及對公共利益的公共領域進行管理的非營利組織。其捐贈受益人包括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與Creative Commons等。
2003年,Young買下了加拿大橄欖球聯盟的漢密爾頓虎貓隊,目前擔任該聯盟的副主席。
2004年,他與Gart Davis領導的出色團隊一起推出了Lulu.com,這是第一個線上自出版服務,可利用按需列印技術幫助新一代的作者直接將作品推向市場,避免了透過傳統渠道出版拖延、浪費以及利潤有限的缺點。在Kathy Hensgen的領導下,Lulu繼續成為幫助作者將作品推向市場的領先創新者。
2012年,Young投資了由Ernie Earon和Christopher Dean領導的小型無人機PrecisionHawk。PrecisionHawk總部位於羅利,已成為美國領先的無人機技術公司之一。他繼續擔任董事長,擔任執行長Michael Chasen。
2012年,Young投資了美國領先的無人機初創企業PrecisionHawk並擔任公司的董事會主席。
自2016年以來,Young一直在跟Scott Mitchell與多倫多的一個團隊合作,幫助組織加拿大自己的職業足球聯賽——加拿大超級聯賽。他是漢密爾頓熔爐隊(Hamilton Forge)的老闆。該聯賽將於本月(2019年4月)開始比賽。
目前他感興趣的專案是幫助妻子Nancy經營Elizabeth Bradley Design公司以及Needlepoint.com商店,這是一家領先的刺繡品供應商。其使命的的確確就是要透過發展壯大全球的針繡愛好者社群,讓讓世界變得更美好。
閑暇時光他最喜歡跟日益人丁興旺的家族共度時光。1年前,他和妻子Nancy迎來了他們的第一個外孫。Young還很享受追求各種愛好,儘管玩得總是很糟糕。其中就包括飛釣、風箏滑板、高爾夫等。最近他還開始收藏起古董打字機了——這可以說是對他從打字機推銷員開始職業生涯的一次致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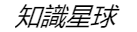 知識星球
知識星球
朋友會在“發現-看一看”看到你“在看”的內容